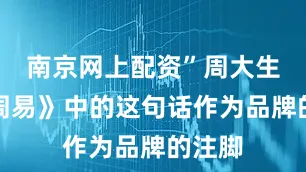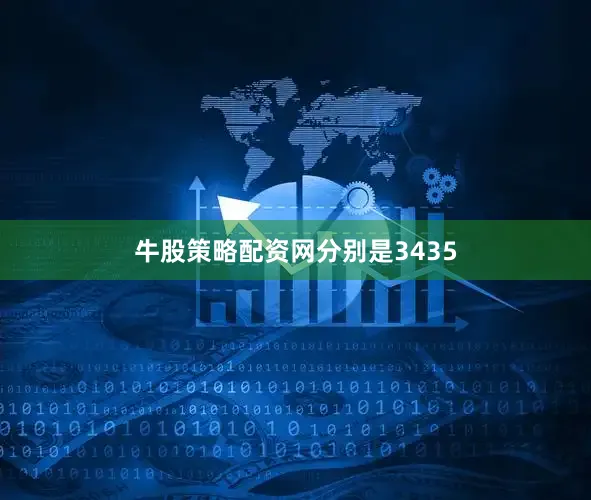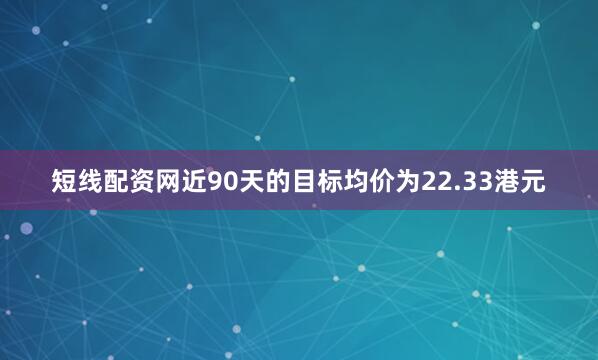你敢信吗?一个地地道道的云南山里娃,竟然能爬到省长的位子上!这事儿搁现在,估计很多人都得琢磨琢磨:“这小子是不是有啥背景?”
从战火中走出的山村娃
咱们得从头说起。1934年,云南那些高耸入云的大山里,一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迎来了他们的儿子——和志强。你想想那个年代,兵荒马乱的,这孩子一出生就赶上了最不太平的时候。
他爹妈就是靠天吃饭的庄稼人,家里穷得叮当响。日本鬼子一来,连山沟沟里都不安生了。炸弹在稻田里炸开花,枪声在夜里响个不停,他妈嗓子都喊哑了,催着孩子们往深山林子里跑。
那年头,地里刨口饭吃都费劲。不过这小子倒是有股子劲儿,跟别的娃不一样。他爹曾经偷偷告诉他:“书能改命运。”嘿,这话他还真听进去了,从来没逃过学。
说起来也怪,别的孩子都在为吃饱肚子发愁,和志强却在那种破环境里学习成绩还拔尖。课桌搬到粮仓里,点着油灯,一群孩子在堂屋里念课文,这画面想想都觉得不靠谱。可就这样的条件下,这小子愣是把书读明白了。
乱世中的坚持换来转机
抗战还没完,解放战争又来了。外面打得乱七八糟的,国共两党干仗那个闹腾劲儿,连山里人都听得见。他爹不敢多说话,他妈就知道叮嘱孩子别惹事。
你知道吗?他同学一年能换三批,走了一拨又来一拨。云南虽然没成正面战场,可压力还是落到老百姓头上了。也有孩子偷跷跑去滇西当兵的,不过和志强从来没动过这心思。他好像早就认准了,只有读书这一条路能走。
新中国成立那年,整个气氛都变了。读书突然成了正经事儿,考大学成了唯一的出路。和志强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拼命学,一点儿都不偷懒。
身边人都说他学得太狠了,吃饭的时候嘴里嚼得慢吞吞的,脑子却还在背地理呢。最后,他考进了重庆大学,这在云南人里头算得上“光宗耀祖”了。

大学里的“较真”学生
到了重庆大学,这小子比谁都认死理。每门课都要刨根问底,连老师有时候都被他问得头疼。你说人是天生爱较真,还是后天养成的?这事儿还真说不清楚。
大学毕业那会儿,分配制度卡得死死的。和志强顺理成章回到云南,进了工业厅的地质队。刚开始分到野外队,他还记得第一次钻进山沟时那股味道——泥土味、露水味,还夹杂着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腐烂气息。
帐篷一扎就是半年,吃的菜常常靠野草凑合,他自己都调侃说:“这地方连苍蝇都养不熟。”不过奇怪的是,他不但没抱怨,反而觉得野外挺适合静心搞技术。
二十年磨一剑的野外生涯
每次把测绘图纸画完,他都把废报纸攒成一摞,跟见到宝贝似的。活儿沉重,可他越干越精。他会用手里的小锤子敲松石头,专挑难走的地方探测矿脉。
他和队友们常年没假期,要不怎么说野外站得住脚才有出路呢?一般人熬几年早就撂挑子了,可和志强硬是咬牙干了二十多年。
别人跳槽转业,他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员爬到了副局长。省地质局的办公室他进去了,副总工的帽子也戴上了,身边人开始尊敬地叫他“和工”。
说到这儿,问题来了:他是因为业务出众才上去的,还是因为“会做人”?局里不少人对此看法不一,谁也说不清楚。
意想不到的政坛跳跃
上世纪80年代,全国改革的声音刚起,提拔干部特别快,知识分子更是受推崇。有人说和志强的晋升像爬坡没阻力,可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。他觉得自己干得还不够,有段时间甚至怀疑新官不适应。
身边人心里清楚,地质局出来的人往往能吃苦耐劳,可管理一个省就完全不同了。他不适应?其实旁人觉得他有时候太“老一套”了。
1983年,49岁的他突然被调进副省长队伍。有意思的是,他刚上任就扑进项目堆里,没人知道滇南边陲条件有多恶劣。花好几个晚上翻地质报告,常常熬夜干到一两点。

两年后又被提到省长位置上,已经51岁了。说到底凭啥省里领导要他做省长,背后的理由多半充满了猜测。当时公认的一条是:他懂地气。
“两烟”战略的大胆布局
云南是全国的“边陲代表”,美得独特也苦得够呛。刚当省长那些年,他上来就抓了两个事——烟草和旅游。
都说“两烟”能救云南,意思是不光要抽的烟,还有烤烟种植。他带人下乡考察村寨,提出烟叶种植要技术升级、管理提升。烟草产业噌噌往上长,那阵子云贵高原贡献了中国相当比例的烟草税收。
他说搞农业必须抓龙头,烟草就得是省级战略产业。这套理念,当地老百姓有人叫好,也有人冷眼旁观。
旅游业的冒险式发展
烟草之外,他又琢磨起旅游业。丽江古城改造、腾冲热海推介、版纳搞旅游开发区——手笔够硬的。他鼓励农民除了种地还能搞热带水果,香蕉、咖啡、橡胶一股脑儿推到市场上。
刚开始农民还挺抵触,觉得新玩意儿风险大。可几年下来流通渠道接上了,农产品外销出现突破。旅游拉动就业,农民也跟着沾光。靠旅游吃饭的家庭一年能多挣三四千块。
不过话说回来,生态压力也开始冒头了。林地遭砍伐、野象冲村子,当时谁也没预见到发展和破坏会纠缠在一起。
基建狂魔的大胆投资
基础设施他一向上心。公路、铁路、水路航空网络一起规划。他壮着胆子拍板高原公路改造,那条连起滇西边陲和昆明的高速,给了西双版纳新的生机。
他说投资要大胆,不能只看眼前,别人却担心工程会成烂账。事实谁也无法预见。基础设施完善,局面大变,云南真的成了西南门户?好像是,可有些成果还真说不清成败。
十三年省长路的功过评说

省长干了十三年,把云南从“小后院”变成了“人来客往”的地方。可也有人私下说,他决策里有点冒险,老农民说他“胃口太大”。城市扩张和土地矛盾也曾引来不少怨声。
不过这不是所有发展都免不了的难题吗?
1998年,这个带着草根气息的省长终于卸下了担子。后来他被任命到全国政协工作,晚年显得低调了不少。身边人对他的评价,褒贬不一。有人感激他拉起了“两烟”经济,也有人说旅游业变化太快,根基不稳。
2007年,和志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没有太多遗憾,他留给云南的,是那段从边陲山村到省府高楼的跨度。农民的儿子成为高官,传奇算不上多大,可人心里多少带着点触动。
也许从一开始,他就没打算当个“普通人”?
时代变迁中的个人命运
云南今天的发展路也不是一帆风顺。把一个省带进新赛道的人,最后也没能控制所有的走向。很多改造带来了新机遇,也藏着没法想象的新包袱。
说到底是冒进还是果断?和志强的经历里,有时候很难清晰分辨。
他用几十年时间脱掉了土布衫,穿上了省长的大衣,可云南的山水还是那副老样子。这里的变化,也像他本人一样,走过了曲折弯道,却总能顽强地延续下去。
聊到这儿,也没个“标准答案”。或许每个人在云南的山谷里,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传奇吧。
你觉得呢?一个农民的儿子能走到省长的位子,靠的到底是什么?是时代机遇,个人努力,还是别的什么?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
配查网-贵阳股票配资公司-配资之家论坛主要有配资炒股-配资门户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